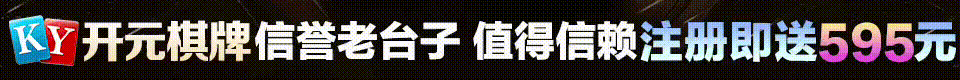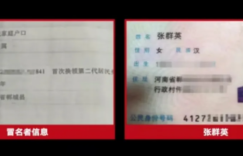2021欧洲杯投注网址-2021法国欧洲杯竞猜-专业外围投注领跑者——2021欧洲杯投注(ozbtz.com)
欧宝娱乐官网登录-欧宝娱乐官网网址-欧宝娱乐官网-欧宝娱乐平台-欧宝娱乐app-欧宝娱乐官网入口——欧宝娱乐(ob6ob6.com)
OB欧宝娱乐-意甲尤文图斯亚洲区域合作伙伴-2021欧洲杯的官方赞助商——OB欧宝娱乐(obob9.com)

今天的故事是【监狱局外人】的第2篇,来自曾经的囚徒何俊义。
他在看守所里呆了一年,期间偷偷摸摸写了份排行榜——被关押人员武力值排行榜。
被他排在第3名的是死囚犯,自己不能活了,下手就贼黑,但往往被锁链限制。而第2名,是拥有武装集团的黑帮老大、大毒枭,得罪他们不仅牢里挨揍,出去也有危险。
我问第1名是什么样的囚犯,他却告诉了我一个匪夷所思的答案——那些艾滋病犯人。
“哪怕这种囚犯再虚弱,但要是想不开了,也不用啥武器,上来就咬你一口。”
2015年,何俊义所处的看守所,迎来了两位艾滋病囚犯。这两位就像行走的炸弹,走到哪,大家躲到哪。
何俊义也害怕,可这两颗炸弹却偏偏找上了他。
那天,阿良坐在自己铺上抠完鼻子,随手就把指甲里的血液弹到空中。
这一下简直像在不到40平米的监室中扔下核弹,其他人看到后,大呼小叫着瞬间逃散开来。监室里乱成一团,我赶紧报告警官。
警官很快带着手铐脚链来了,让我把阿良铐起来。
我小心翼翼地走向刚才被我喝令进卫生间里待着的阿良,阿良放出那无辜的眼神,可怜巴巴地说,“哥,我做错什么事了吗?”
我气得差点把十几公斤重的锁链甩到他脑袋上。
阿良20岁,生得一副好面孔:瓜子脸、小嘴巴,对人微笑时,表情温柔得如春风拂面。我第一次见到他,还以为是个误入看守所的良好青年。
但藏在这副温柔面孔下的,是被艾滋病病毒侵袭6年的身体。阿良的血液指数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阶段,但凡有点儿风吹草动就可能丧命。
说起自己的染病过程,阿良像是在讲笑话。
14岁的时候强行拉一个女孩子进旅馆房间,女孩子不让他搞,警告说她有病。精虫上脑的阿良却以为女孩子在开玩笑,霸气十足地说,“怕个卵,老子也有!”。然后就真遭了。
阿良这次是因为贩毒进来的,是他人生中第二次因贩毒入狱,但他这次的案子有些特殊——警方在交易地点不远处还抓到一个人,阿良的同案陈君祥。
阿良在现场被抓获时手里的毒品只有1克多,但坐在一边车里等他的陈君祥身上还藏有20多克。麻烦就麻烦在,两人被捕后给警方的口供并不一致。
阿良说自己只是陈君祥的小弟,不知道陈君祥身上有毒品;而陈君祥却说自己没有参与阿良的贩毒,身上的毒品是用于自吸的。
警察一时之间无法定性那20多克毒品,也分不清谁是主犯、谁是从犯。
其实案子的事情不归看守所管,进来的也没人在意别人啥命、咋判,但好巧不巧阿良被关到了我们监室,这就让每个人都绷起了皮。
监室里死刑犯、大毒枭、涉黑大佬等等加起来就有十几个,平时哪一个都不是省心的料,现在监室里又来了阿良这么一个艾滋病犯人。
祸不单行的是,阿良的同案,“大哥”陈君祥被分到了我们隔壁监室,进来体检时才查出来,也有艾滋病。
这俩人的出现让我们这片监区里、外的生存难度直线上升。
虽然知道日常接触没问题,但我们这个“日常接触”和普通人的实在没法比。
我们是坐牢,监室巴掌大的一块地方,同吃同住同上厕所,24小时凑在一起,而且还不是消停待着,时不时就要动两下拳头,结了梁子还会被暗地里报复回去,说心里不发憷绝对是假的。
任谁都想躲,可麻烦却偏偏落在我头上。
监室的主管孙警官找到我,给我安排了一个艰巨的任务——做监室里的“耳目”,盯着点这俩人别出乱子。
阿良是“三无人员”,即:无衣物、无汇款、无信件。这种人哪怕在看守所也是最让人瞧不起的角色。
但阿良在我们监室里混得还可以,一来是大家本来就躲着他,二来阿良特有眼力见,会“办事”,嘴还甜。
我们通常不给艾滋病患者安排劳动,因为害怕他们乱碰东西,但阿良会抢着帮人干活,吃过的碗、脏衣服,直接拿过去就洗。
他因为艾滋病发烧,医生来的时候他极其配合,认真吃药之余还不忘对着医生真诚的鞠躬致谢。
知道我是监室的二把手后,阿良就自来熟地拉我手,轻轻地摇了摇,说:“哥,放心,我懂规矩。”
平时我除了尽量跟他保持距离,对他也没有特别的防范,看在他生病的面子上,还给了他优先刷牙洗澡的待遇。
结果阿良和我熟悉后,开始来搂我肩膀跟我称兄道弟。我提醒他,“摸一摸,三百多”,想让他少跟人肢体接触,避免引发别人的恐慌。
他只是笑眯眯地说,“怕死的老板不是好大哥。”然后还是该搂就搂。
他对自己的病似乎根本不以为意,吃饭时,他甚至会直接把自己的勺子伸到别人碗里舀一口。
和阿良在监室里上蹿下跳如鱼得水的状态不同,他的大哥陈君祥像一块沉在水底的石头。
这段时间他的日子很不好过。
他是进了看守所体检才知道自己得病的。床铺被安排在监室的最角落,大家都躲开他。
被号长安排最后一个刷牙,最后一个吃饭,最后一个上厕所。每次上完厕所后,必须要蹲在便池边用旧毛巾、旧牙刷,一点点擦洗干净。
这意味着,他不仅要清理自己的,还要清理其他人残留的排泄物。
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很可能摧毁一个正常人。
我曾经看过隔壁监室的监控,在时长接近一个小时的画面中,陈君祥脑袋低垂,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不动。但有些行为又很奇怪,比如:喜欢看其他人洗澡。
每天到洗澡时间,陈君祥会把头扭向监室后面的洗漱区,右手撑起脸颊,专心致志地盯着看。
陈君祥上厕所的姿势也跟别人也不一样,他每次解小手都是蹲着,期间会拿水桶放在腿边遮挡,解完之后还用卫生纸仔细擦拭。
阿良那样咋咋呼呼搞动静的还好,反倒是像陈君祥这种状态,在看守所里才是最恐怖的。
我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人,如果不重视,很可能哪天他就会突然悄无声息地自杀。陈君祥是艾滋病人,我们很担心哪一天他会突然爆发或者害了同监室的人。
而且最近陈君祥的情绪突然有所起伏,昨晚还躲在被窝里哭,可问他为什么哭,他又摇摇头死咬着嘴唇。
孙警官说,陈君祥之前那就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独生子,小学和中学都在重点学校就读,大学毕业以后进入航空公司当空乘,简历堪称完美。人无不良嗜好,跟“犯罪”完全不沾边。
家庭条件也不错,进来不到两个星期家里就来送过五六次全新的衣物,不是阿迪达斯就是耐克,打来的生活费也有数千元,还帮他请律师。
只是父母从没来看过,也没让律师带过话。
我和孙警官都很纳闷,就算陈君祥以前有毒瘾,也不可能依靠卖“零包子”(零包子指少量的毒品)来支撑生活,他怎么会跟阿良这种二流子扯上关系呢?
为了摸清陈君祥的状态,孙警官去隔壁监室把陈君祥带出来跟我见面。
之前在监控里看得不太清楚,我没发现陈君祥长得竟然挺帅气。快35岁了,脸上却没什么皱纹。穿着一套浅色运动装,浓眉大眼,身材很好,目测接近180cm,乍一看像个明星。只不过给人的感觉并不自信,一直低着头。
我尝试着打开话题,先提起了艾滋病,我说我也不太懂这艾滋病会有啥症状,阿良最近就发了两次烧,顺势问他有啥不舒服的地方。
陈君祥没有回答,反而是他抬起头一脸担忧地问我,阿良怎么样了,好点儿没有?说着说着他的眼眶似乎有些红了,搞得我莫名其妙。
他问我:“我这里有些消费票,帮我带给阿良,可以吗?”
我说好。
然后他翻空自己衣服裤子上所有的口袋,掏出藏在里面的票子递给我。
我算了一下,告诉他一共有580元,开玩笑地说:“你是新客户,我免你一次手续费。”
陈君祥对我的调侃无动于衷,又想了一会儿,说:“还我60块,拿给他520就好。”
这次送钱过后,陈君祥仿佛把我当成了快递员,每次跟我见面不是带着衣物被褥就是带着钱,让我全部转交给阿良。
我看着陈君祥的衣服越穿越破,到后来除了内衣之外,只套着看守所发放的也不知道是过了几手的简易马甲。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,结果他回答,“只要阿良过得好就行了,我穿什么都一样的。”
我明白了这两人一定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江湖大哥和小弟,只听说过小弟伺候大哥的,没听说过大哥掏光所有去供奉小弟的。
我向孙警官汇报了我的疑惑。这两人的关系估计并不简单,这场贩毒案怕是要有变数。
而得到陈君祥送来财物的“三无人员”阿良,陡然暴富之后的行为却也让我大为困惑,他并没有使用,反而是仔细收藏起来。
我问阿良,为什么不用?他说,几个月就出去了,用不着。
我暗暗的想:你当我傻的呢?那20几克要是算到你头上,你搞不好会就死在监狱里。
一个月后,阿良把陈君祥送来的所有衣服和票子包成一大袋,托我拿给陈君祥。我发火了,骂阿良说你们真当我是快递员了!
阿良再次展示他那楚楚动人的温柔,说:“哥,你就帮帮我嘛,好不好?”
我答应了,心中的疑团却再一次凝聚:这两人到底是啥关系?
第二天,我提着阿良打包好的东西拿给陈君祥。陈君祥看到包裹,瞬间泪崩。
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我面前梨花带雨地哭,我多少觉得有些尴尬,问他要不要把东西还回去。
陈君祥说好。然后问我阿良还说了啥。
阿良确实有托我带话,“我可能要被判7、8年,也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满刑,但是没有关系,你能出去就好,如果我死了,记得给我烧香。”
阿良说自己愿意承担那20多克毒品的责任,打算下次提讯时告诉警方自己才是贩毒的人,陈君祥只是个不知情的司机。
陈君祥听到哭得更厉害了。
缓了一会,陈君祥终于抽抽嗒嗒地承认,他和阿良其实是恋人关系。
那个我们眼中的“二流子”阿良,是陈君祥心里唯一的依靠。
那年,陈君祥30出头,那是他第一次鼓起勇气去同志酒吧。
“酒吧的灯光很昏暗,放着轻音乐。每张桌子都坐了不少人,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,我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。”陈君祥形容道。
他记得以前被同事拉着去过的酒吧,那里音乐震耳欲聋,场地气氛热烈,人们往来穿梭,就算是不熟悉的人也会端着酒杯到处串台认识新朋友。
可同志酒吧如此不一样,大家只是围坐着,仿佛都有自己的小圈子。舒缓的环境渐渐稀释了陈君祥的冲动,他有点慌。
陈君祥坐到吧台,点了一杯啤酒,忐忑不安地抿了起来。他期待会有人跟他搭讪,问他是“0”还是“1”之类的问题,然而并没有人理他。
实际上,如果真的被人问起来的话,陈君祥也不懂该怎么回答,他只知道自己是喜欢男孩子的,但并不确定自己是倾向于男性角色还是女性角色。
就在这个时候,阿良过来搭讪了。
陈君祥对阿良的第一印象是很帅很健谈,讲话的时候会层出不穷地丢包袱,而且尤其勇敢,因为第一次见面,他竟然就向陌生人承认自己是同志。
阿良说这话的时候落落大方,仿佛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。陈君祥很佩服他的勇气,因为他在二十年的生活里一直压抑着自己的内心。
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点不一样是在初中时。当时校花写了封满是古诗词的情书给他,他看完后有些排斥,这种感觉怪怪的。
到了大学,他跟一个长得也很漂亮的女孩子去开房。她洗澡的时候,陈君祥看到了女性的裸体,然后那种感觉又来了。最后陈君祥不顾女孩子的挽留,抓起自己的东西冲出房门,落荒而逃。
从那以后,陈君祥成了同学们茶余饭后的笑料,大家背地里说陈君祥阳痿,“不是男人。”
陈君祥很喜欢看男生光着膀子打篮球,他也渐渐明确自己是喜欢男孩子的。但他太优秀了,他心里隐隐不能接受自己不喜欢异性这一点。
陈君祥不敢跟父母坦白,只能试探性地告诉母亲,自己好像不喜欢女孩子,母亲说可能是没有遇到合适的女孩子。陈君祥也开始这样认为,他甚至觉得自己这样是一种病。
空乘本是个令人羡慕的行业,在07年时,毕业生年薪就能达到20万,但对于陈君祥而言,这种优秀反而增加了他的负担。
不仅如此,在空乘圈子里,男女关系混乱,和男同事间的话题往往离不开这些,和他们去酒吧时,也总被怂恿着去搭讪女性。陈君祥觉得和女性接触很恶心,比较抗拒,相应地,跟同事的交情也没有太深。
跟世俗格格不入的陈君祥觉得越来越压抑,交际圈变得越来越小。到最后借口家里离单位远,自己在外边租了个房子住,连应付父母的日常都省略了,一下班就往出租屋里躲。
“那时候,我觉得仿佛整个世界都找不到一个能够理解我的人,我快要崩溃了。”但他又害怕别人指指点点,甚至不敢去找心理咨询师。
而当他去到酒吧,看到阿良坦荡荡承认自己是同志的那刻,他感到很羡慕。他觉得那就是自己一直幻想能拥有的东西。
那天晚上,两人在酒吧聊得很开心,酒一杯接一杯,暧昧的气息逐渐发酵。
出了酒吧,两人便直奔酒店而去。
陈君祥从来没跟男性发生过关系。
学生时代的他只要帮男生递水,就觉得很幸福,心里特别满足。后来到了单位,看到那些刚毕业的小鲜肉会很兴奋。
为了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,他只能看小黄片。他下载了所有能下载的片子,一部接一部看,边看边把自己带入幻想。幻想的对象有时候是那些打篮球的男生,有时候又是单位里的同事。
但是每次想到睡在他们旁边的是个女人,陈君祥又觉得有点恶心。
到了酒店后,两人脱了衣服,陈君祥有点茫然。回忆到这时,陈君祥一脸幸福,“他还吹牛说自己身经百战呢,其实也是个新手。”
不过,和同性做爱并没有陈君祥想象得那么好,“就好像在完成一套工作流程。”
他最喜欢的反而是跟阿良紧紧抱在一块的温暖,还有第二天早上阿良帮他挤好的牙膏、搭好的毛巾。
一夜后,两人迅速进入到热恋状态。陈君祥不知道阿良具体是做什么的,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感情。
陈君祥出差多,但每天晚上都要跟阿良煲几个小时的电话粥,听着阿良不停地呢喃“亲爱的”才能睡着;而回来之后,下飞机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阿良,叫他去单位旁边订酒店。
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待在酒店里,出去时总是手牵手。起先,陈君祥还有点在意,因为他害怕周围人投过来的目光,提议要戴口罩。但阿良一点不在意,当着路人的面大方地亲吻、拥抱他,这让陈君祥觉得踏实又安心,也慢慢放开了。
压抑多年后,这段自由对他来说是那么宝贵。
“艾滋病是那时染上的吧?”我问陈君祥。
“嗯,不过也没啥,染病就染病吧,我不怨他。”
陈君祥当然明白染上艾滋病意味着什么,但查出来的那一刻,他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行,只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靠墙的角落,把耳朵贴到墙上——
墙的另一边是我们监室,那里是阿良在的地方。
但两人过往的回忆在阿良这里可没有那么多浪漫色彩,他不会刻意去记什么相处的细节,所有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都可以简单归结为一场戏?一个计划?或者,单纯是一张饭票,一条生路罢了。
用阿良自己的话说,“我就是一块在火锅里煮太久的肉,烂到连筷子都夹不起来了。”说这话的时候,他脸上甚至带着笑意。
和陈君祥一路光明的人生坦途不同,阿良的人生似乎从一开始就是困难模式,前一天晚上闭上眼就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命看到明天的太阳。
他不知道父母长什么样,是外婆带大的,不过,所谓的带大也只是有个睡觉的地方,吃的是百家饭,有一顿没一顿的。村子里的孩子常常以食物做交换,让他去砸别人家的玻璃。
小学没毕业就出来混江湖,很快染上了毒。出去混也是运气最差的,跟过几个大哥,但大哥们一个个都“半途而废”踏上了改造之路,只有他还在腐臭的泥沼里挣不上岸,因为14岁那年染上了艾滋病。
其实,14岁的他根本不懂艾滋病意味着什么。因为潜伏期很长,他染病后看上去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,身体状况也没受到什么影响。以为不过是场感冒。
但在阿良没有察觉的时候,他的人生已经悄悄开始烂了。
有次进戒毒所,没关两三天就被人家放出来了,理由是:不收艾滋病人。怎么连戒毒所都不敢收呢?戒毒所不是国家的吗,我这病国家都不敢关吗?
14岁的孩子第一次有点害怕了。
他不知道怎么办,他想活,但似乎找不到好好活的路。他开始贩毒,告诉自己要“尽情享受人生”。终于,又一次被抓。这次被关进了专门收监艾滋病人的监狱。
他在里面看到了那些早已过了潜伏期的艾滋病患者:黑肿的脚踝、溃烂流脓的皮肤、熄灭了光亮的双眼,只剩一副空瘪的躯壳。
那里让他想到了深渊、地狱。
他意识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变成那样,就像地狱里的一只孤魂。
或许是觉得自己已经跌进地狱了,他在监狱并没有悔过,“既然没什么活头了,干脆死之前潇洒起来。”艾滋病监狱里有很多毒鬼,他在里面问别人怎么拿货、讨教制毒的配方。
被放出去的那一刻,钱成了阿良眼里唯一能看到,也是唯一能给他安全感的东西。
他知道同志中有很多“药娃儿”,于是那天晚上,他混进酒吧寻找目标客户。
推开门,陈君祥就坐在那里。
“卖身”给陈君祥后,阿良其实并不缺钱,陈君祥每个月给他的零花钱差不多有5000元,这是他贩毒所挣不到的。
然而阿良没有跟陈君祥天长地久的打算,他想的是开拓自己的贩毒之路,只等上正轨后就离开陈君祥。
有一次两人在酒店,阿良掏出一小袋毒品,神情飞扬地说对陈君祥说,吸这东西后特别持久。
陈君祥其实无所谓这些,对于他来说,有阿良在身边就已经很满足了,床上的事儿属于锦上添花。两人中拿主意的一直是阿良,陈君祥没有阻止阿良,心想只要阿良高兴,就由着他去吧。
但阿良不仅自己吸,总是怂恿陈君祥尝试,美其名曰“你也哄哄我嘛”。热恋中的陈君祥对恋人的邀请难以拒绝,很快也染上了毒瘾。
看到陈君祥染毒,阿良觉得是时候亮出自己的计划了,他跟陈君祥说自己想贩毒,还有了贴心的理由,“总不能老是没钱了就伸手向你要,我也想独立。”
吸毒是一回事,贩毒则是另一回事,陈君祥心里明白其中的差别。他苦口婆心地劝阿良,可阿良怎么会听陈君祥的呢?
原本在阿良心中,跟陈君祥在一起就是意料之外的事情,这时候发现陈君祥竟然不支持自己,毫不犹豫就提出分手,还删了陈君祥的微信。
率先作出决绝姿态的那个人总是占着心理优势的。陈君祥没能坚持两天就投降了,他疯狂地打电话给阿良,说自己错了,求阿良不要走,自己愿意支持阿良做任何事情。
阿良当然不是真的要丢掉饭票,不过是演戏罢了。见陈君祥认输,阿良抱着陈君祥发着誓哭了一场,之后就开始用陈君祥给的本钱大量进货,打算要狠干一场。
陈君祥并没有察觉到阿良藏在眼泪背后的心机,那时候他只顾得庆幸于挽回了初恋。
或许是因为失而复得的缘故,陈君祥更加珍惜阿良了。
陈君祥的工作很忙,常常要跟机飞往全国各地,一去就是好几天。阿良常常抱怨陈君祥对他不管不顾,快活一晚后扔点零花钱就走,自己像是个被包养的宠物。
为了陪阿良在一起,陈君祥开始有了推脱工作的苗头,远的不想飞,近的嫌麻烦,到后来都不愿意去上班了。这种态度终于让单位失去耐心,领导找他谈了一回,说要么老老实实上班,要么干脆滚蛋。
陈君祥去征求阿良的意见,没想到阿良却劝他一起贩毒,这样两人就能天天在一起了。
陈君祥选择了爱情,最后还是辞职了。他以为阿良也跟他想的一样。却不知道他极力维护的爱情,其实只是阿良眼中的生意。
但他说自己并没有真的参与贩毒,只是偶尔开车送阿良去交易。
辞职后的日子很快活,两人手牵手逛会儿夜市,大部分时间里,两人选择的是窝在床上,点几百元一只的海鲜、几千块钱一瓶的红酒,这些都是陈君祥出钱。
“那是我最幸福的日子,他对我特别好,吃东西都要喂我,我差不多胖了十斤。”陈君祥说。
后来由于两人开销过大,陈君祥的存款很快就被花光了。他先是卖了自己的车子,然后又把母亲送的手表卖了,最后恨不得当掉身上的名牌衣服。
而这一切都只为了讨阿良的欢心,“阿良以前没过上好日子,我想努力让他体验奢侈的感觉。”
正当陈君祥不知道该如何维持生活的时候——警方把两人双双摁在了贩毒的路上。
被抓那天,阿良正在出售一包1.59g的冰毒,放在一个“苦荞茶”字样的黄色塑料袋里。陈君祥骑着蓝色摩托车把阿良载到了某家酒店门口去做交易,自己在附近等着。
陈君祥当时身上也有20多g冰毒,他坚持说那只是用来自吸。
我自认已经明白目前的局面了:爱情的事儿,陈君祥是一厢情愿,阿良是边打边弃胡;而贩毒的事儿由阿良一手主导,但资金由陈君祥提供,因此他们的案子应该不分主从犯,估计两人都要判7年以上。
两人的口供无疑成了判决的关键依据。
但原本普通的案情在两人的恋人身份暴露后变复杂了,因为谁也不知道,他们会做出怎样的证词。
孙警官担心两人的状态会被案子影响,再反过来影响判决,还会给监室带来麻烦。于是,为了稳住陈君祥,从而稳住阿良,他同意陈君祥和阿良之间互相递东西,只要不违规就行。陈君祥知道后难得地露出了笑脸。
陈君祥让我带话给阿良:我们都要坦白,争取从宽处理,这次犯的事情不大,几个月就能出去,之后两人一起努力,痛改前非以迎接幸福生活。
回去之后,我跟阿良开玩笑,问他和陈君祥什么关系,他说陈君祥是他老大。我说陈君祥跟我都坦白了,他才不好意思地承认。
听到陈君祥的话,阿良陷入了沉默。
其实陈君祥这话说得有些想当然了,但凡进过监狱的人都知道“坦白从宽,牢底坐穿;抗拒从严,回家过年”,而且陈君祥肯定不懂毒品案的判罚条款。
他以为他们贩卖的只是1克多,而那20多克会以“非法持有”来定罪,这样的话,两人的刑期是一年左右。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,在办案单位的概念中,只要嫌疑人有贩卖的行为,那么身上藏的毒品也会定性为贩卖。
但无论如何,这套稳定情绪的方法奏效了。那之后,陈君祥自我封闭的状态确实有所好转,他开始主动和别人聊天,主动跟号长要求帮忙拖地、晾衣服。
对看守所里的人来说,劳动就代表着希望,能让失去自由的人不至于堕入胡思乱想的境地,导致悲剧。
与此同时,阿良的状态反而开始变得不稳定了。
阿良不正常地连续发了3次烧,每次都在《新闻联播》开始之前。那时候是看守所一天中最安静的时段之一,他能闹得整个看守所都听得到。
跟以前一样,我发现病情后立刻呼叫医生。而不料这3次,阿良都有抗拒行为,不是说医生开的药没用,就是埋怨看守所的医疗条件不好。
这些话引得医生破口大骂:“你以为你是进来旅游的!有药给你吃你就该感谢国家了!”
阿良还主动申请戴戒具,吹胡子瞪眼,动静极大,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,就只差跟医生对骂了。
这时我才大约猜出阿良的目的,他没有办法直接跟陈君祥说上话,因此想闹大动静来告诉陈君祥自己过得很不好,而且撑不了多久了。
他在赌一个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事,陈君祥对他的爱。
回忆起酒吧的初次见面,阿良后来告诉我,当时他看到陈君祥盯着酒杯,耳朵却竖了起来想听别人说话,以为陈君祥是来酒吧买“货”的,于是试着去搭话。
他根本就不喜欢男的,更没想过会发生之后的事情。
或许从一开始希冀一个14岁就得了艾滋病的人充满希望和勇气地大胆追爱,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。
我问他,那为什么要跟陈君祥上床?
阿良眼神闪烁,不好意思地说:“哥,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。”
他想活,无论那代价是什么。
过后不久,阿良托我给陈君祥写了一封情书。
同案间传递信件属于违规行为,我将此事报告给孙警官,也说出了我的疑惑:阿良很可能是故意发烧的。
陈君祥搞不清楚状况可以理解,但阿良这个二进宫,心里一定清楚,按陈君祥说的那样肯定是不可能轻判的。可他还是让我把包裹还给陈君祥,跟我说自己几个月就能出去了,他这是在打什么算盘?
孙警官说故意发烧应该不至于,阿良掌控不了自己的身体,而且他也不是舍得拿命去拼的人,但是报告的时间和跟医生的争吵一定是他计划好的。
至于写情书的事情,孙警官说你能写就写吧,因为贩毒的资金是陈君祥提供的,他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,如果此时不能维持陈君祥的幻想,指不定会闹出多大的麻烦来。
他一直认为自己被阿良深爱着。
那封写满3页纸的情书极其难产,足足花了20天的时间。阿良口述,我来下笔,他再亲自照抄了一遍。
阿良早早辍学,字体写得一塌糊涂,情书的内容更是像流水账一般毫无吸引力。他先是回忆两人相遇的经过,“认识你是我最大的运气”;然后再说到在一起的甜蜜,“鱼儿在水里,你在我心里,鱼儿爱水,我爱你”;最后是煽情——
“如果一起认罪,两个人都要死。如果你认罪,我不认罪,我能出去,但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可活,出去了也没用。所以不如我先死,你出去,我们下辈子再聚。你出去之后帮我买一套阿迪达斯吧,就是你最喜欢的那套,你穿起来特别好看,我也想穿,然后跟你一样好看。”
可就是这些在我们看来水平极低的文字,却把陈君祥感动不已,捧着信哭了老半天。
最后连孙警官都看不下去了,找了个借口骂我:“写信就写信嘛,为什么要涉及案情?难道还要我教你规矩?”
陈君祥知道,孙警官这是在提示他可以回信,连忙擦了一把眼泪,跟孙警官说想给阿良写回信,劝阿良摆正心态,不要胡思乱想,安静等待判决结果。
孙警官同意了。
而就在走出警官办公室的时候,陈君祥偷偷拉了拉我衣袖,在我耳边轻轻地说:“帮我告诉他,好好活着,一切有我。”
我当时根本没意识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
过了几天,陈君祥趁着孙警官埋头整理资料的时候,迅速把几张信纸塞到我怀里。我吓了一跳,心想警官都特许你写信了,干嘛还搞得神神秘秘的。
陈君祥却眼神复杂地看着我,眼眶里的泪水呼之欲出。
眼泪在看守所里是最不值钱的东西,我有些厌烦陈君祥的哭泣,觉得他堂堂一个七尺男儿,动不动就泪眼朦胧,一点儿骨气都没有。然而不知道为什么,那一刻我就是心软了。
回到监室后,我把信交给阿良。阿良看完信后,一只手捂嘴大笑,眼睛眯成一条线;另一只手捏成拳头,在空中挥了几记无声粉拳。然后拿出储物箱里的花生瓜子,请监室所有人一起吃。
他穿的每一块布、吃的每一颗豆豉都陈君祥给的。
陈君祥写信的水平比阿良高得多了,信里说:岁月如河水一般,我知道它最终会流向大海,但我还是希望沿途中能见识到壮阔的波澜,而与你相遇,就是我生命中的波澜。这段时间我在想,如果你是浮在我这条河上的小船,那我就要把你安全地送到海岸。
最后还来了一段:“那套阿迪达斯你自己去买吧,我不能陪你去了,但是你穿的时候能闻到我的味道。别死太快,等我出来,抱抱。”
这时我突然能把所有的线索联系起来了,之前阿良打包衣物也好,叫我传话也好,包括这次写信,都是装可怜,目的是为了要引导陈君祥主动去承担罪行。
这个案子说起来复杂,实际上对阿良来说还是有解套的办法——只要陈君祥承认自己是主谋,说阿良只是个打工的,那么阿良就能以“从犯”的角色得到轻判。
之后我离开看守所去了监狱,直到2019年刑满释放,回到家后才在网上看到了他们案子的结果。
判决书上显示,陈君祥是主犯,刑期8年,阿良是从犯,刑期9个月。
阿良赌赢了。
我没想到,阿良那一封写得有些可笑的信能够导致现在的后果。
孙警官后来告诉我,收信后陈君祥可能在监室偷偷查阅法律书、请教其他毒贩,然后提交了应对办案单位的另一套说辞。
陈君祥曾跟我说过,“你们都看不起我,但是我不介意。我知道被他骗了,可是如果不跟他在一起,我又能怎么样呢?染病了是要死,我也怕,但我不后悔,至少我知道什么叫恋爱了,这总比一个人闷闷地活着强。”
我想起他坐在靠墙角落的那个画面——
把耳朵贴在墙上,听隔壁我们的声音,不时幸福地笑着。
没人知道他到底听到了什么。
也没人能替他决定这一切究竟值不值得。
挺多人的童年阴影,就是父母老提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但像陈君祥这种别人家的孩子,其实也可能在煎熬地活着。
他要戴着这层面具,抵抗自己真实的感受,在众人的期待之下活了30多年。
他为了维护这些形象,只能小心翼翼地向最亲的人透露自己可能不喜欢女孩子,试探失败就迅速收回,独自陷入同志是种病的困境中。
当遇到主动的阿良时,他才有机会面对自己的内心,只可惜对方却是假意。
他最后选择独自承担8年刑期,不仅是因为爱,反而更多地是对压抑自己过去的强烈反抗。他揭下了那维护已久的面具,代价惨烈。
或许每个人都有面具,很难立刻摘下,但也可以时常发问:我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?
本文来自投稿,不代表博信博彩资讯网立场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bx365.ph/156215.html
刊载的文章由平台用户所有权归属原作者,不代表同意原文章作者的观点和立场
乐天堂FUN88官网-乐天堂FUN88备用网址-乐天堂FUN88官网-乐天堂FUN88平台-乐天堂FUN88app-乐天堂FUN88官网入口——乐天堂FUN88(f88dh.com)
欧宝娱乐官网登录-欧宝娱乐官网网址-欧宝娱乐官网-欧宝娱乐平台-欧宝娱乐app-欧宝娱乐官网入口——欧宝娱乐(388ob.com)
迈博myball最新网站|迈博体育官网|最好玩的体育直播观看平台——迈博体育导航(mbo388.com)
蜗牛娱乐|蜗牛德州|蜗牛扑克|蜗牛娱乐官网|蜗牛娱乐唯一备用网站——蜗牛备用网址(ggallnew.com)
大发体育Dafabet|大发体育官网|dafa888|大发娱乐场——大发娱乐城(dafa22.com)
乐天堂彩票-极速快乐彩、时时彩、北京赛车等多元彩票玩法,立即下载APP送38元——乐天堂fun88(fun888.xyz)
以上资讯由爱博扑克论坛(www.pukebodog.com)整理发布!